邹易辰,2010年9月生,就读镇宁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四年级,爱好:打乒乓球、魔方、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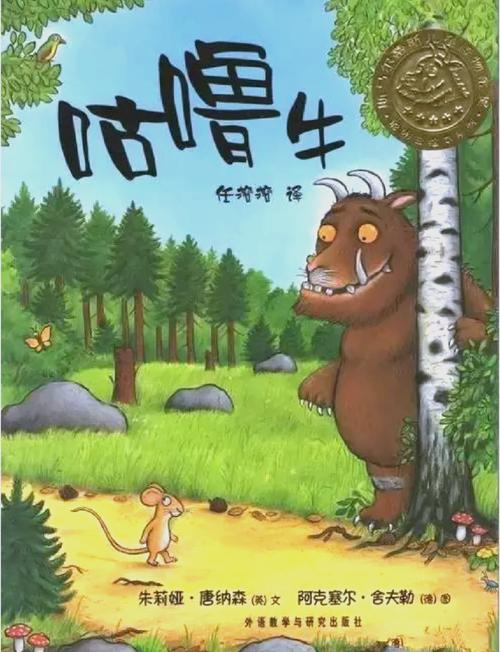
我的妹妹,超级可爱的“小牛”,虽然可爱,但是生气时就像《斗牛图》里的“牛”,可狠了,她全副武装,用尖锐的“牛角”把我顶撞在墙角,真是“牛劲十足”。“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她眼里,从不畏惧“牛高马大”的我。
见我闲着,她便撒娇对我说:“哥哥、哥哥,我要骑黄牛。”我便撑在地上,她蹦蹦跳跳地骑上我背,手里拿着玩具钢琴边弹边唱,手舞足蹈地命令“黄牛”走快些,仿佛让你感受袁枚写的《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时而爬在“牛”背上抚摸,顽皮够了,“小牛”都会伸出双手竖起大姆指说:“哇,哥哥你牛、真牛!”那表情让人忍俊不禁。
这就是———我的妹妹,可爱的“小牛”。
迈着崭新的脚步迎来2021年,我和“小牛”妹妹要向“牛”一样,做一个勤劳踏实、顶天立地、坚强不屈的好少年。
>>>>>>>>>>
李玉荣,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报刊部负责人、编辑、记者。
如果大黑牛还在,到现在已十多岁了。只可惜五六年前,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大黑牛是我家和姑爹家共同喂养的一头牛,也是我们寨子里为数不多的一头牛。每年春耕是大黑牛最忙碌、最劳累时节。
这也难怪。除了我家和姑爹家的春种外,大叔二叔家要栽洋芋,首先想到的是大黑牛;三叔四叔家要种包谷,想到的还是大黑牛;寨子里好多人家的春种,想到的还是我们家的大黑牛。
父母亲不止一次夸说,大黑牛真是一头好牛。寨子里使用过大黑牛的每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大半辈子养过好多牲口,像我们家大黑牛一样的牛从来没有遇到过。
大黑牛刚来我家时还是一头小黑牛,壮壮的,肥肥的,长得相当可爱。那是夏天,牧草茂盛,父亲不但经常夜半三更给小黑牛添加草料,还常常叫侄儿侄女一有空就割草喂牛。父母亲去做农活时,小黑牛就在庄稼地边悠闲地啃噬青草。小黑牛在我们一家人的精心饲养下,长得很快。到了秋天,父亲便开始训牛了。外侄牵着牛,父亲驾着犁,开始让小黑牛学翻土。通过数天训练,小黑牛踏上了“正路”。再听话的畜牲也有兽性大发的时候,为了更好地训牛犁地,父亲还穿通牛鼻子,系上一条长绳。想不到牵牛鼻子这一招,盗贼也用到了大黑牛身上。
发现大黑牛被偷走的那个早晨,父亲一路沿着后山墙边飞奔而去,汗水流满了父亲的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期间由于心急还跌倒了好几次,手也被荆棘刺伤,鲜血流淌不止,父亲依然没有停下寻找的脚步。可是,天不遂人愿,父亲除了发现大黑牛留在村庄里的几个脚印外,再也没有找到大黑牛。
大黑牛被盗走的时候,正是要翻地为来年备耕播种的农忙时节。我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迅速从城里往乡下老家赶。到家时,家人已报了案,说听后通知。可是,直到现在,我们家依然没有听到有关大黑牛的一点儿消息。
母亲难过地说,大黑牛实在太可怜了,头一天还犁了一天地。母亲指着狭小的墙洞口说,这么小的洞口,盗贱把它强行打拉出来,肯定疼死它了。我安慰母亲说,盗贼认钱不认牛,他哪管这些。况且寨子里不也只是我们家被偷,大不了再买一头来喂养,以后注意防范就是。可母亲一再说,这么好的大黑牛被偷走实在太可惜了,都怪我们没有看护好。我一转脸,发现一旁沉默不语的父亲深深的垂着头,凹陷的眼眶,噙着泪花。
有空闲坐时,我们一家常常提起大黑牛。父亲常常说:“如果有来世, 大黑牛现在也变成一头大黑牛了,只可惜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
李磊:牛与土地
李磊,2020年毕业于贵州财经大学,现供职于中国银保监会黔南监管分局
辛丑牛年将至,关于牛的回忆,一下全部涌入脑海,伴随着键盘的敲击声慢慢铺陈开来……
我模糊记得我家养的第一头牛是水牛,他高大威武,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走路总是注视着远方,好像永不服输的样子,两只对称的大牛角,长得快要弯起来变成一个圆了。那时候我大概三四岁,对于它的记忆,仅仅止于此。后来,听爷爷讲,在牵他去耕地的途中,由于路滑不幸摔下山坡,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上个世纪末,对于完全依靠牛耕方式来种植庄稼的爷爷来说,大水牛与土地和我家的永久离别,确实让他很伤心。但是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农民家庭一笔收入的损失,更是人与牛、牛与土地感情纽带的消逝。
我家养的第二头牛是一头黄牛,他毛发光滑金黄,在阳光的照耀下,似火红色般,听老人说,这种颜色是黄牛最上乘的颜色,寓意着他有火红的未来,也能为农民带来丰收的秋天。它头顶上还有一小朵白色长毛,这种黄牛更是少见,属于杂交牛的一种类型,其品种特殊,所以在习性上有别于一般配种的黄牛,杂交牛最大的优势就是生长快、力气大、好喂养,这几个优点完全符合农民养牛的标准。
这头黄牛陪伴了我大半个小学时光,我的童年也是和它打交道,早上出门给它割草准备食料,下午放学就和小伙伴们约起上山放养。那段短暂的童年时光,虽然枯燥、辛苦,也没有手机等娱乐工具的陪伴,唯有一起长大的玩伴和一头黄牛,但那时候却过得非常快乐,充满了无限的乐趣。黄牛从幼年走向成年,我们也一年年长大,昔日的放牛娃走出了那座大山,走向他们小时候梦想的舞台。如今,一个个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有的在县城当上“小老板”,有的在沿海城市打工挣钱收入可观,有的大学毕业考上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他们正如那头老黄牛一样,几年如一日默默耕耘,厚积薄发,用自己的汗水和付出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如果说土地是农民的根,那么牛就是充实那一片热土的魂。那头老黄牛,从春天插秧的稻田到秋季播种的旱田,都有它低头奋进的身影,为我家种地立下汗马功劳。
现在,爷爷年岁已高,亦不能像年轻那会儿继续在他热爱的那片土地上劳作,岁月更替,时光流走,在他心底的那份老黄牛精神一直发挥着热量和温度,激励着我们勇往前行。
“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自无一毛利,主有千箱实。”立春时节,戴着斗笠、背着蓑衣的老农牵着勤奋的老黄牛漫步在田埂、行走在乡间,恰似一幅春耕细雨图。那一片我深爱着的土地,那一头值得回忆的老黄牛,都化作绵绵伟力,催我奋进。
>>>>>>>>>>
张维:牛年话牛
张维,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桐梓县文学协会主席,现供职于桐梓县融媒体中心。
纵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十二生肖,没有哪一种属相不是人们喜爱的。没有谁去给生肖排过名次,但牛起码应该是名列前茅。因为牛厚道,实在,能忍辱负重,乐于奉献。
读过初中的人都知道“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等等,不一而足,都是对牛的赞美。
牛是吉祥物,是许多民族崇拜的图腾,是美好生活的象征。在我国乡村有牛过年的节日,也就是正月初五这一天,农民不忘牛一年的辛勤劳动,要特意给牛做好吃的。还有贵州苗族的牯藏节,以及一些民族的祭祀等活动都是对牛的崇拜。无论什么形式,都体现了人们对牛的喜爱和崇敬之情。甚至人们在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也用牛来寄寓美好的期盼和祝福,如“牛犇”“牛奔”“牛得草”等。
我们刚刚历经鼠年疫情。否极泰来。牛年,牛气十足,我们以拓荒牛的精神奋力开拓创新;牛年,我们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埋头拉车;牛年,我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魄,披荆斩棘;牛年,我们为人处世不钻牛角尖,不“强按牛头饮水”,尊重他人的意愿和选择;牛年,做事牵着牛鼻子,抓住要害,不对牛弹琴;牛年,我们继续弘扬老黄牛的精神,牛劲十足,辛勤耕耘。牛年,我们一定能够获得六斋兴旺,五谷丰登,汗牛充栋的好收成!
>>>>>>>>>>
王彦月:牛与牡丹
王彦月,笔名峻皎,2001年3月出生,现就读于重庆市重庆工商大学,家居贵阳。
“嗯,好甜”我皱皱眉头,庆幸终于没有再吃到酸的了。
橙黄的皮掉了一地,我头上的枇杷树还在摇晃,碎掉的阳光扫过我的后颈,我蹲在哪里,只沉溺于刹那间的甜蜜。
果林旁是一片空地,稀稀疏疏种了几株花,那时我本该捧着课本,执笔苦苦计算,但始终受不了枯踩的压制,同友人跑到乡野偏僻处。
我头大,漫长且无情的数字逼我要不知从何捏造的结果,关键是试卷上猩红的分数,瞬间顿失了人间希望。
于是我计划了逃离。在枇杷树下肆无忌惮地松懈些,远处山坡上阴一块亮一块,葱葱不变的披装大抵又换过一年。
山下是牡丹园,当然也有兰花之类的贩卖。
我转头看到果林旁的空地。空地上花开了,稀落的几棵牡丹,几朵红花坠着重瓣,随风摇曳着。
空地左斜旁的小道突然迎来了新客。我不认识来客,因而会面更有趣味性。
红艳艳的花突然晃动几下,继而淹没进褐口的一开一合中,花没有了,我望见来客顶着两个灰蒙蒙的角,侧头,迅速地嚼完那朵花。
嗯?我停下来,手里还剩一口的枇杷掉下三个核。
来客并没有淡然地离开,红色还留在它黑色的唇上,下一秒,他扬起两只前蹄,在空地上欢快地跳了起来,鼻环也随之晃动。
我似乎听见它的欢叫声。“去!”空地上又多了其他人,把裤脚高高卷起的放牛人手里还拎着几棵花菜,此时,我才明白它原也不是散漫的。
我把最后一口枇杷塞进嘴巴里,它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我,我也看着它。
偷有的快乐,充斥着两双眼睛。
纯粹的坦白在我们之间展开,它平静下来,随着放牛人远去,我意识到花已经吃完,枇杷也只剩下了核。
果林迎来一阵滔风,拂散焦热,更多的枇杷掉落下来。
倘若没有痛苦的点缀,常有的幸福也不过平淡。
那朵牡丹花,一定很甜。
>>>>>>>>>>
曹海玲:戏里戏外话“牛人”
曹海玲,一级编剧,贵州省省管专家,享受国务院和省政府特殊津贴,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作品有黔剧《天渠》《腊梅迎香》,京剧《锦绣女儿》,话剧《出山!》《青春百分百》,舞剧《蝴蝶妈妈》,音乐剧《血丹砂》,木偶神话剧《黄果树瀑布传奇》,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西湖歌·湄江谣》等20多部。出版专著《曹海玲戏剧作品集》、新编史剧《亚鲁王传奇》。
报社邀约叫我说说牛年,才意识到这个曾经让我们痛彻心扉,也曾让我们生死共渡,也曾被人间的爱拯救的鼠年庚子,就要过去了!牛年说些什么呢?还是想说说那些在戏外深深打动过我,我在创作的戏里又打动了更多人的那些“人”。在我的创作生涯中,他们的苦难命运,他们向死而生的生命力爆发,是如此集中而频繁地撞击心灵,是我始料未及的。
黔剧《天渠》的黄大发,黔剧《腊梅迎香》的邓迎香,京剧《锦绣女儿》的石丽平,话剧《出山!》那些叫得上名字叫不上名字的乡里乡亲。他们在高山河渠绝地突围,向天借水,向地要粮;他们在荒瘠深处,痛定思痛,换个活法;他们被命运一巴掌打倒在废墟上,又浑身血肉模糊地爬起来的人;他们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痛苦地如同蝉儿蜕变般觉醒继而完成命运自我救赎、人生逆转的人,都说他们是贵州的“牛人”。我把“牛人”们的很多故事写进了戏里,但在采访他们时还有不少故事留在了戏外,就讲两个戏外“牛人”的故事吧,他们虽没有直接入戏,却是我在塑造“这一个人”的过程中,“牛人”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在大时代变迁中人情人性的表达。
邓迎香,带领村民10多年硬生生打通一条穿山隧道,在众人眼中,她是女汉子、当代女愚公。动笔前最后一次去见她,那天风很大,也许同为女人,惺惺相惜,心意一通,便聊得深。“我心里有苦,有委曲,人前从来不哭,可一到擦黑,一头倒在床上,一个人抱起枕头哭……我好孤独,好累哟!”“是不是想过不想干?”我看到这个女汉子迎风落泪的脸。“不行啊,还得接到干。”“为什么?”“我们麻怀走到现在太不容易,我是邓迎香,我没有选择。”真的没有选择吗?不,作为一个“人”,她在失儿丧夫后做过离开还是留下的选择,在无数个孤寂的夜晚,做过放弃还是坚持的选择,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她自己看得见的内心深处,徘徊,挣扎,在多少次人生选择的锻造中,开辟出牛人的崭新内心世界,牵引我们用戏剧带领观众去发现贵州“牛人”背后“一个完整的人”的人格魅力。
黄大发,时代楷模,悬崖上凿出一条生命水渠。80多岁的老人,早就从支书岗位上退下来,可他天天上渠,当然是职责所在,使命使然。那一次聊了他女儿的很多往事,女儿是黄大发此生心上永远的痛,也是一个父亲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他突然抹了一把泪说:“这条渠就是我家闰秀,我天天上渠,走走看看,就是要去见她的。”我深信,天渠,是一个时代楷模的天地胸襟,也是一个老父亲难以释怀的情感寄托,“英雄”两个字背后,是血和泪,是戏里戏外的契合,方筑贵州“牛人”的精神硬核。
戏里戏外的魅力,在于探寻人性人情的多种可能,牛年新春将至,等待我和我们写好未来,当舞台那束光亮起,那条光道是由戏外引向戏里的艺术通道,经由更多精彩动人的故事和人,抵达你的心海。
>>>>>>>>>>
袁本良:苏轼写牛
袁本良,1946年12月生,1970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汉语教研室主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古汉语语法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2006年12月退休。现为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修辞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语言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
《说文》云:“牛,大牲也。”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之中,以牛为大。几千年的中国农耕社会中,牛不仅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决定因素,还对中华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汉语中与牛相关的语词和典故可以说是多如牛毛;而前人诗文中写到牛的作品更是汗牛充栋。以苏轼作品为例,其诗词中写到牛的地方就有130多处。
苏轼一生坎坷,虽历经宦任,更多的时间却是遭到贬谪流放。他以亲身劳作养家活口,所以跟牛的关系十分密切。居黄州,他在东坡开垦种植,“农父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流寓儋州,“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外如“晨与鸦鹊朝,暮与牛羊夕。”“笑我一生蹋牛犁。”“松风溜溜作春寒,伴我饥肠响夜阑。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都可以看出他对牛的特别看重。
苏轼诗云:“卖剑买牛真欲老,乞浆得酒更何求。”“卖剑买牛”这样的话,他的诗词中曾经四次说到。他又以牛自喻:“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在一篇题画诗中,他更发出“世间马耳射东风,悔不长作多牛翁”的喟叹。由此可见,诗人对牛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爱写牛的苏轼,他的诗真的“很牛”。
>>>>>>>>>>
戴明贤:牛杂烩
戴明贤,1935年生。西泠印社社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牛年将至,命题作文随之来袭。搜索枯肠,材料库竟毫无一点有关材料。窘迫中忽忆起在儿时的家乡,北校场的军号一响起来:咪哆索--索索哆--;顽童们就引吭响应:猪大肠--羊杂闹--。干脆就烩一盘牛杂碎交差,行不行听便。
县城的孩童常见马过街;少见牛犁田。牛之受我的关注,回忆起来应该是《西游记》《封神榜》里面太上老君的坐骑青牛,与闻太师的墨麒麟姜子牙的四不相等同属神物。牛魔王已经变作人形,一直忽略了它也是牛。后来知道了故事的原型是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被关尹强留写下道德经,这才省悟青牛就是常见的水牛。再有就是选入国文课本的《儒林外史》第一回,王冕给东家放牛把书挂在牛角上,到地方牛自吃草他自看书;读了书也不去考官,自己做诗画画。这个王冕和他的牛对我毒害很大,从此认定干哪一行都不如读书自在。
后来很喜欢看李可染先生画的水牛牧童。搜了很多不同画面的印刷品,百看不厌。我们省的宋吟可先生也是画牛圣手,求他画过一开册页。当场画,一头浮在浅水里的牛,一个骑在牛背上的牧童娃娃,不到一分钟时间。另一开红梅,也是半分钟。神乎其技!国画中水牛常见,黄牛只见过一幅五牛图。对于国画(尤其是水墨画),客观事物有的入画之有的不入画。水牛入画黄牛不入画。竹鸡入画锦鸡不入画。茅屋入画华厦不入画。
对真牛的记忆,一次是在花溪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吃了中饭步行进城,走到甘堰塘,见一人一黄牛在前面走。牛若无其事地走着;见路边有草就伸嘴尝尝;人若无其事地跟着,闲着手里的小树枝鞭子。走近一搭讪,是畜牧站职工送牛去贵阳。清早动身出发的。到甘堰塘正是一半路,算来要天黑才能到地方。我想,他完全可以带本书边看边走;或者像契诃夫《苦恼》里的那个马夫,把一肚子的烦恼都说给这头好脾气的牛。像这样走一整天哑巴路真能闷死人!另外,有一回刚过了10周年国庆,宣传系统职工到洛湾参加秋收劳动,重九那天吃现舂的糍粑,说是牛王节,慰劳牛辛苦。那时三年困难已初见端倪,我们没有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传统,自行开伙;常有当地小孩远远站着看我们吃饭。三年后我和一批文友奉调到南白镇三岔河写报告文学,农户菜地已恢复,我们饭食很好了。晚饭后在大树下桥栏上乘凉,常赶上牛队从山上回村。艺高胆大的牧童们比赛着站在牛背上呼啸而下,煞是好看!牛队经过的时候,我发现水牛们居然眼神悲哀,很诧异。后来写进文章,发表时擅自删了。可能他认为牛不可能有悲哀的眼神。我小时候,接触到的多为汉族,十有九家不吃牛肉的,认为牛为人终生服役,不能劳其筋骨还要食其肉。猪就不同,就是喂来杀吃的;一年到头,吃了睡睡了吃,最后虽然献出生命,连人都是谁无死呀!
总之,在我记忆中牛都是正能量的形象。诗人也咏牛不咏猪。乾隆皇帝想了句夕阳芳草见牧猪,自以为得所未有。其实别人是认为猪不能寄托人格。南宋抗金名将宗泽咏病牛说: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弱卧夕阳。肥猪怎么咏呢?
股市出现后,见把旺市称为牛市,很有些不解,觉得牛是任重道远的象征。后来见到内行人的解说,感叹不同民族的文化,能相异如此。而把牛作赞词:你真牛!又可视为从善如流了。
>>>>>>>>>>
编者按
牛年到来的时候,贵州画家陈争画的高坡牧牛图,和全国各地数位画牛名家的作品一起,在《中国书画报》上呈现。即使各有“牛气”,但贵州画家最懂贵州牛,陈争笔下的贵州水牛的强悍和不屈,完美呼应着新时代贵州故事中无处不在的坚韧气质。在辞旧迎新,举国上下“牛气冲天”的振奋和愿景里,贵州人也需要用自己的笔墨、自己的表达,迎接充满无限可能的新的一年。
天眼新闻文化频道、27°黔地标读书会特此推出“牛年说牛”话题征集,你可以说关于牛的成语和典故,也可以说身边的牛人、乡村的牛市,还可以说养牛或者斗牛的精彩片段,当然,对牛年表白一下你的新年愿景也不错……反正,牛年来了,就让我们用各种关于牛的讲述,让它从一开始就有模有样、如火如荼地“牛”起来!
欢迎参与“牛年,牛得很”话题征集活动。
稿件要求:散文、随笔类,1000字以内;请附200字以内个人简介及形象照片两张备选。
投稿邮箱:gzrb27@qq.com。
截稿时间:2021年2月26日9:00。(执笔:舒畅)
文字编辑/舒畅
视觉/实习生 文俊
编审/李缨




